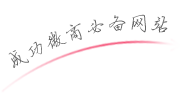- 首页
- 微信群
微信群大全 创业群 辣妈群 互粉群 微信福利群 微信红包群 麻将群
- 地区微信
- 个人微信
微商微信 模特微信 交友微信 宝妈微信 女性微信 吃货微信- 微信公众号
微商公众号 搞笑公众号 教育公众号 兼职公众号 娱乐公众号 营销公众号 电商公众号- 微信货源
“桃花园”:亦真亦幻,既喜且忧
发布人:admin / 发布时间2022-03-02 15:08:22 热度:“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渊明的这篇《桃花源记》是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渊明的这篇《桃花源记》是流传最广的古文之一,千百年来,“桃花源”已经成为中国人恒久的梦想。 《桃花源记》面世一千六百年后,陈亮写出了长诗《桃花园记》,两者题名高度相似,文字重合率75%。无疑,它们之间有一定的互文性,《桃花园记》有着对“桃花源”的致敬与重写。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渊明的这篇《桃花源记》是流传最广的古文之一,千百年来,“桃花源”已经成为中国人恒久的梦想。 《桃花源记》面世一千六百年后,陈亮写出了长诗《桃花园记》,两者题名高度相似,文字重合率75%。无疑,它们之间有一定的互文性,《桃花园记》有着对“桃花源”的致敬与重写。与“世外桃源”不同,陈亮的“桃花园”是现实的。如果说“桃花源”是出世的,“桃花园”则是入世的。 “桃花园”来源于生活,是与泥土、粮食、村庄、家族具有同等意义的存在。正如陈亮自己所说:“《桃花园记》是我平生第一个长诗,几乎融入了几十年来我对这个时代的最多感受、认知和艺术呈现。这里面有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的青年、我的中年,或者无数个‘我’的少年、青年和老年的影子,既是个人的又是众生或时代的。 ”这个“桃花园”是“我的”,也是“我们的”,构成了“我”和“我们”的生活世界,与人的现实生存、命运遭际息息相关,同时也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感。
另一方面,“桃花园”又是虚构的,是幻象的、艺术化的。“桃花园”从其现实层面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却又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的系统,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这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应该不无关联。陈亮的家乡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距离不过几公里,许多的“魔幻”或许本身就是这片土地上的“现实”,它们共同指向了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的最深层、潜意识层面。就此而言,“桃花园”是“托寄物”,用以表达作者的情感、价值取向和文化关切。例如诗中的“我”不是写作主体的我,而是有着明显的虚构性,是一场戏剧之中的一个“角色”,类似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而“桃花园”一定程度上也可与“大观园”相比,“和很多人一样,我在桃花园里出生/小时候却长得矮小,体弱多病/性子天生内向、柔绵,偏爱孤独的事物”“我信赖的玩伴几乎全是丫头/她们善良、柔美,我们经常腻在一起/我相信她们都是桃花托生的”“在桃花园,我是个特别爱哭的孩子/会经常为一朵云哭/为一根草,一棵树哭,一把弹弓哭/为一道墙上的裂缝哭/一阵风,一只鸟哭,为母亲哭”。 “我”在精神气质上与女子、与桃花高度契合,而对仕途经济毫无兴趣,与贾宝玉几无二致,他们与人生的关系都是超功利的、审美的关系;他们柔弱,却又体现出“真的人”的可贵品质。 “桃花园”外表是实的而内在则是高度精神性、文化化了的,是虚的。这种“虚”是为了表达更高程度的、现实中含纳不了的“实”。
“桃花园”是一个家园、一个归依。 “我”在这里获得内心的平静、安宁与喜悦,这里面有着文化上与情感上发自内心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桃花园是原乡,是来处也是归途,是世界的中心与边界,有这样的所在,内心是幸福的、欢喜的。
而在这欢喜背后也包含着隐忧,以及挥之不去的暗影。在《桃花园记》中,忧戚是大于欢喜的,从本质来讲,“桃花园”属于农业文明的产物,在与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较量中,其“节节败退”是必然的,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唯其如此,更需要对过往的文明形态进行审视,因为其中包含了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所包含的诸多经验与教训。在这方面,陈亮可谓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冷静地谛视农业文明之衰落这一历史变局,内心不能不喜忧参半、五味杂陈。现代人已被数量、速度、效率所挟持,如诗中所写:“那里人山人海,都在玩一种/垒积木的游戏,看谁垒的积木不会倒塌/垒得越高,奖励越多,财富越大/有的人竟因此成了“英雄”/周围掌声雷动,让人感到诡异的是/那些掌声竟然出自一群鬼的手心//以至于很多人和积木绑在了一起/将自己的心血全给了积木/牺牲了官职和性命来玩积木”,这种“变形记”显然是具有现实性的。那个爬眺望树眺望的傻子“闲蛋”挂在嘴上的“快来了,快来了”有如谶语,“仿佛不经意间扔过来一块石头/每一次都会让我的心里慌慌的/每一次我都会感觉周围的树在摇晃/屋子在摇晃,人也在摇晃、模糊/让我感觉要地震了”。在这里,主人公的态度是矛盾的、左右互搏的,从情感上,他自然是高度认同的,而从理智上,又不得不面对它的衰落甚至消亡。全诗最后一节“桃花仍将灼灼盛开”,是一种美好期待,符合“我”的情感逻辑,而现实场景却是:“人生纵有良辰美景,也终有散场的时刻/推土机推土机——我已经隐约听见推土机/从远方向这里掘进/他的轰隆声,他搅起的滚滚烟尘/隐藏了蚂蚁般喧哗的人群/一切都将消失,仿佛一个巨大的泡影”。当然,这也并非终点,而是获得新的可能性的起点。
“桃花园记”亦真亦幻、既喜且忧,构成了一个极为丰富的艺术空间。或许可以说,“桃花园”是一个现代的“桃花源”故事,它承载着梦想,构成永恒的召唤,而又不脱离时代境遇,面对困难,寻索当代的方案。
作者简介:王士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分享到朋友圈
 精选文章
精选文章- 03-03 字母哥利拉德缺阵 约翰逊领衔3人20+篮
- 03-03 英超-加克波世界波萨拉赫破门 利物浦3-
- 03-03 詹姆斯31+10库里38分 里夫斯突破绝杀湖
- 03-03 新赛季中超限薪不加码 职业联赛引援选
- 03-03 斯诺克世界第一特鲁姆普成为香港居民
- 03-03 CBA常规赛第21轮最佳阵容出炉 上海男篮
- 03-03 NBA周最佳球员出炉 文班亚马和坎宁安分
- 03-03 2024国际乒联第52周排名公布 男女单打
- 03-03 CBA一周综述 | 上海“咸鱼翻身” 辽宁
- 03-03 中美“乒乓外交”53周年纪念活动在洛杉
- 03-03 吴柳芳再被禁言 掉粉600多万 目前粉丝
- 12-31 今年我国竞技体育获世界冠军数量创历年
分享家规则

- 1、第一分享家好处是什么?
-
1)文章会挂上你的二维码提高爆光率
2)分享出去的文章你就是作者
3)将会获得网站金币
4)首页推荐快速加粉丝
5)像公众号一样传播你的文章
- 2、如何成功激活分享家?
- 任何微信搜索用户都可以成为分享家,您只要把任何一篇文章成功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必须是微信朋友圈,分享到其他平台是激活不了的哦),系统就会立即自动激活您成为分享家。
- 3、如何成为第一分享家?
- 第一分享家是分享家族中最高荣誉,在分享家族中分享同一篇文章贡献值最高的用户就是该文章的第一分享家。
- 4、怎样统计我的贡献值?
- 贡献值是来自您分享文章到微信朋友圈好友的访问量,访问IP次数越多,贡献值就越高。同样您朋友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您分享的文章,其贡献值也是属于您的。朋友帮您转发的越多,您的贡献值就会更高。
 保存图片后,随时访问手机端!
保存图片后,随时访问手机端!